阅读:0
听报道
我们主编朱伟最近出了一本书《重读八十年代》。书里介绍了上世纪80年代几位比较重要的作家,比如王蒙、王安忆、陈建功、余华、莫言、史铁生、苏童等。每个人单独一章,通过与这些作家的交往,牵扯出那段时期中国小说的动向、潮流,质朴的时代背景,以及对诸多作品评论。虽然谈及的作家不多,但已经初步勾勒出那个阶段文学脉络。我想,朱伟是有野心的,可能还会重读出好几本书,毕竟王小波、阿城、王朔们还没登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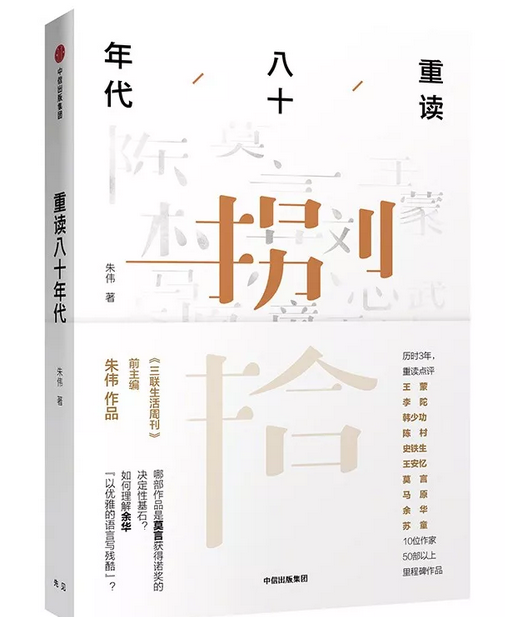
苗炜从来都直呼朱伟为“老朱”,还写过一篇文章《一直特立独行的老朱》。虽然朱伟也退休了,我也离开了《三联生活周刊》,但多年来我一直习惯叫他主编,直呼其名总感觉有些冒犯。写这篇文章,又不能张口闭口“主编”,所以,就别扭地“冒犯”一次吧。
《重读八十年代》这本书的写作结构基本是,朱伟是怎么认识这个作家的,与他们是怎么交往的,他们的作品是怎么出来的,在当时的影响以及后来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多年来,朱伟一直在幕后工作,知道他的人不多,尤其是年轻一点只知道自媒体不知道媒体是怎么回事的人,对这个小老头更是知之甚少,你在百度上得翻到第八页才能在百科里看到有关他的介绍,可见他是叫“朱伟”的名人中名气最小的。我记得有一次洪晃采访朱伟,问他为什么能当好主编,朱伟说,我坐得住,不像你跟交际花似的。
所以,我也得从认识朱伟开始写起,这样可以有机会让更多人了解他,即使不买排名也能在搜索引擎中排得靠前一点——但这个前戏可能略微有点长。
一
2001年上半年,我相对比较闲,因为处于失业状态。时任《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的苗炜问我能不能开个音乐专栏。我之前从未开过专栏,反正有大把的时间,就试着开始写。大约过了半年,苗炜又问我有没有兴趣来周刊工作,我稀里糊涂就答应了,在此之前,我都没看过这本杂志。
去《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就要走一个形式:见一见主编朱伟。

关于朱伟,江湖上有很多传说,总之是个很厉害的人,经常骂人。我战战兢兢去了安贞大厦的《三联生活周刊》的编辑部。正好在楼道里碰见朱伟,周刊的一个记者介绍说:“主编,这个人就是王小峰。”朱伟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然后转身走了。
我的面试是在楼道里通过的。
在去《三联生活周刊》之前,正式的工作我换过十六个,却没想到在周刊一待就是十六年,直到2017年离开。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在这家杂志“存活”这么长时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伟。
我完全是误打误撞进的媒体,没有特别扎实的写作基础,尤其是到了周刊后,肚子里仅有的那点墨水很快就倒光了。2003年非典,我突然失去了状态,连续几周没有发稿。朱伟把我叫到办公室,质问我为什么不写稿。我说是因为非典,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所以写不出来(这也叫理由?)。朱伟很严厉地说:“下周你要不交稿子,就滚蛋!”
大约过了小半年,我才写了一篇周杰伦的封面故事。这期间有好几次被朱伟叫到他的办公室训话,每次他都说:“下次再让你来我办公室,就是让你滚蛋的时候。”
我后来也发现,只要一有天灾人祸的事情发生,我就没有状态,写不出稿子。比如2008年地震、奥运会。整个2008年,我几乎没写什么稿子,年底,朱伟找我谈话,意思是你还想不想干了。我说,今年就算了,我心还在梦还在,只不过是重头再来。
2009年1月1日一大早,朱伟就把电话打过来了:“你不是说今年要写稿子吗,已经2009年了,你该写稿子了。”挂了电话,我乐半天,他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其实我很清楚,在周刊工作,压力很大,积累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够,而我又是个生性比较散漫的人。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朱伟这么宽容的人。别人对你宽容,意味着自己更要有自知之明。我还算有一个优点,工作起来比较认真。
朱伟给所有同事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个暴躁易怒的人,空旷的办公室常常回荡着上海普通话口音的骂声。不知有多少同事,因为受不了朱伟的羞辱,含恨离开了周刊。每次被他骂,我都会想,自己还有哪些问题,虽然主编可能有些固执,但是他的经验一定比你多,肯定是自己的问题。事实也证明,《三联生活周刊》后来有一定影响,成了媒体的一个品牌,跟朱伟的“暴行”有很大关系。

印象中,朱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篇采访该怎么写,不该怎么写,他只用发稿和毙稿两种结果告诉我稿子写得怎么样。每次被毙稿,我都要反省半天。
领悟这事儿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但是前提是你要看到并捅破它。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朱伟骂跑。
二
朱伟是个很勤奋的人。
在我去《三联生活周刊》之前,就有人跟我说,朱伟每天早上五点钟准时起床,然后写东西,最后写出了一本厚厚的《音乐圣经》。
我去了周刊之后,终于领教了他早起的厉害。我做封面故事,第二天交稿,头天晚上九点多坐在电脑前磨蹭,直到后半夜才开始写,而且必须在朱伟起床后检查邮箱的时候让他看到稿件躺在收件箱里才行。有几次我拖拖拉拉到了早上六点还没写完,朱伟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你不是说早上交稿子吗,怎么现在还没给我?”
《三联生活周刊》改成周刊之后,每期要发大约20万字的稿子,朱伟要在每个周末把这些稿子看完改完,相当于两天看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一看就是二十年,换个人大概早就崩溃了。

他写《重读八十年代》这本书,要把那些作家的作品都看一遍,保守地说也得看五百万字吧。没点认真和勤奋的劲头,是做不下去的。
跟朱伟共事这么多年,我发现,他是一个不管跟你说什么都是在很严肃地跟你讲道理的人,很多人不喜欢听人讲道理,我正好相反,在周刊这些年学到的很多东西多是听他讲道理得来的。
因为朱伟过于严肃,所以少了一些幽默感,比如他不太会开玩笑,从他嘴里开出的玩笑往往会让人很尴尬,笑也不是,哭也不是。他对笑点的理解很像中国足球队前锋对球门位置的理解,但大家也习惯了。有一次我给《生活圆桌》写了篇随笔,可能是字数有点多,发稿时删掉了一些文字。出刊后,苗炜悄悄地跟我说:“你最后抖的那个包袱被朱伟删掉了。”我说那前面的铺垫不成废话了吗。苗炜说:“他们上海人可能都不听相声。”
后来我长了个心眼儿,给周刊写稿子,尽可能不抖包袱,抖的话也不要放在文末,以免被删掉。
三
在工作中,朱伟是个恶魔,生活中他却是个很有情调的人,尤其是退休后,养养猫狗,拍拍花草,聊聊节气,读读古诗,晒晒美食,看看夕阳,恍如生活在别处。他身上颇有些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如果他生活在唐朝,那些咏梅咏雪咏馒头的诗就没别人写的份儿了。
在朱伟众多的爱好中,最大的爱好可能就是古典音乐了。他听古典音乐的时候激光唱片还没面世。有一次我去他家,看到二楼的过道摆满了唱片,我迅速地长乘宽乘高粗算了一下,大约有六千多张。

我对古典音乐涉猎不多,主要兴趣是流行音乐,所以不敢在朱伟面前班门弄斧。有一次,我去淘唱片,买了两张德国一家唱片公司出的比较偏门的古典音乐唱片,送给朱伟。因为上面都是德文,我看不懂,只能看出来是哪个乐团演奏谁的作品。
朱伟看着这两张唱片,给我讲了俩小时这两部作品是怎么回事。最后说:“流行音乐太简单,信息量太少,以后要多听听古典音乐。”
我去周刊不久,朱伟在郊外买了一套房子,还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那地方特别远,我想他可能在城里住了好几十年,嫌闹,所以才搬出城住。后来我一研究,发现不是,这肯定是跟他听音乐有关。
原来周刊在北三环安贞桥边上的安贞大厦,朱伟家离单位不远,开车20分钟就能到单位。朱伟喜欢开车时听唱片,可是一张唱片少说也得有45分钟,刚听一半就到地方了,怎么办呢?他为了把唱片听完,只能在单位或家附近继续开车绕几圈再上楼。这事儿挺困扰他的,于是决定搬家。
别人买房子都是要考虑户型、价格、面积、物业、交通、周边业态……朱伟买房子只考虑一件事——和单位的距离。他往车载音响里放进一张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然后从单位出发,一路向北。
为什么要放一张《贝九》呢?是因为当时CD唱片最大容量是75分钟左右,能容下最长的交响乐作品就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马勒的《第三交响曲》太长,只能录成双张唱片。
这要感谢当年索尼电器公司的大贺典雄,在上世纪80年代激光唱片推出之前,索尼与飞利浦公司在唱片容量究竟该有多长时间的问题上出现过分歧,飞利浦认为应该是60分钟,这和一盘卡带的时间一致。但是大贺典雄认为,一部交响乐的时长超出60分钟是常事,60分钟的激光唱片会让很多交响乐作品无处安身。在经过反复论证之后,决定以能容下《贝九》的时长为一张激光唱片时长标准,这就是过去一张激光唱片只有75分钟的原因。
也就是说,朱伟未来住的新家,与单位之间的距离至少路上要完整放完一张《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才行。距离不够,《欢乐颂》正唱到高潮部分,到家了,这时候关掉音响该有多难受啊。
当《贝九》在雄壮悠扬的合唱声中结束,朱伟把车停下,放眼望去,有很多楼盘,可以在这里买房子了。但朱伟还有点不放心,毕竟不同指挥家、乐团演奏的《贝九》版本不一样,时间有长有短。他回到家,把手上所有不同版本的《贝九》都找出来,发现卡拉扬、伯恩斯坦、莱因斯多夫、阿巴多、巴伦博伊姆、君特·旺德、布隆斯泰特、霍格伍德、弗里乔伊、克伦佩勒、加迪纳、布鲁诺·沃尔特、富尔特温格勒、奥曼蒂都指挥过《贝九》,为这事朱伟开车去了十几趟郊外,算上路上的红绿灯和高峰时期塞车的时间,找出平均值,最终选定了现在的家。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一段里程和它播放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朱伟是个很讲究生活细节和品质的人。
但是朱伟没有得意多久,周刊编辑部就搬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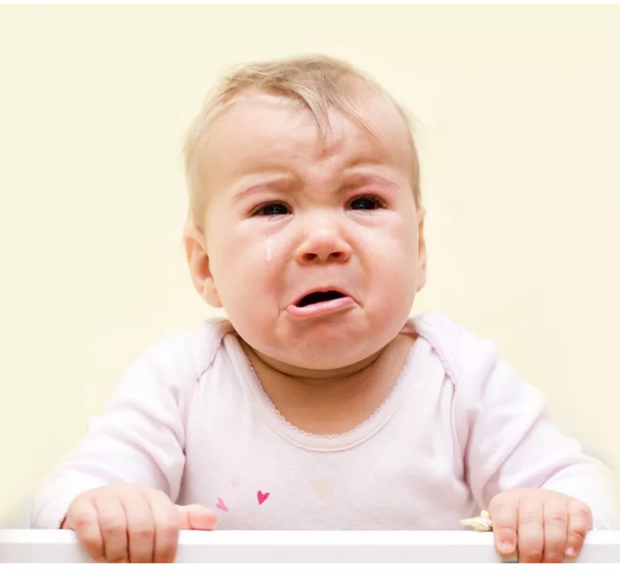
四
现在进入正题,说说这本《重读八十年代》。
一般人们热衷谈论的过去,往往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这和史学家研究历史完全不同),比如当下中国人都喜欢谈论唐朝,谈论民国。大概是时间、距离产生一种幻象的模糊美吧,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未必觉得好。通过想象制造一种虚幻,是非史学者们喜欢谈论历史的方式。
作为一个逐渐步入老龄社会的中国来说,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80年代,但你很少看到人们去谈论这个年代——因为它还没有被虚幻化,还太真实,还有记忆。以世俗的标准来看,80年代跟今天比,显得太粗糙,太低级,太土气,照相机连美颜功能都没有。那个年代的人不知道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都会坚定地认为,明天会更好。
有些东西确实是因为技术突破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现在最烂的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都比当时最好的单反胶卷相机拍出来的照片要清晰。我们没有理由去怀旧,去留恋,那个年代本应该是留给三百年后的后代们去想象的——就像我们今天梦回唐朝一样。
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却和时代、技术的发展背道而驰,变得无比丑陋。丑陋的时代、丑陋的灵魂如何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呢。读《重读八十年代》,我的思路总是跳跃到我熟悉的流行音乐领域,80年代的流行音乐和当时的文学何其相似啊,比如书中朱伟经常谈到的笔会、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谈论文学、谈论现代派,这些在音乐圈里也经常出现,80年代在北京音乐圈里有很多沙龙,音乐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展示自己的作品,音像出版社的编辑觉得哪首歌好,就会找到歌手,进棚录音。
甚至在对西方文学营养汲取的方式上,也几乎和流行音乐模仿西方音乐一样。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是一片空白,你可以去任意泼墨挥毫,不管外来的东西搞没搞明白,先用上再说,创作者都在尽一己之力去拓宽创作的疆界。80年代的文学、艺术,在今天看来,有些幼稚原始,但生动生猛,所以才会出现至今让人念念不忘的作品。它本来应该在完善中成熟,结出更多的硕果,但是很遗憾,几年的光景它便陆续夭折,文学、电影、戏剧、音乐在进入90年代中期后,像沙漠里的季节河,一点一点地断流了。
我想,朱伟花了几年的时间去重读八十年代那批作家的小说,不仅是因为他亲历了那段文学的辉煌时期,值得去特书一番,可能更是因为对后来文学的失望。
那个八十年代,只能重读,不能重返。
五
朱伟正式在《人民文学》杂志做编辑,应该是1983-1992年这段时间。我也从高中考上大学,并毕业走向社会。我还清楚地记得,高三的时候班里偷偷传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课余时间同学们除了聊金庸、梁羽生,也聊张承志、史铁生。那时候你不知道几个作家,没看过几部小说,跟现在的中学生不知道吴亦凡鹿晗TF Boys一样丢人。
上大学后,图书馆里的纯文学杂志一直是抢手货,因为我当时迷上王朔,到处找王朔的小说,这才发现,图书馆里的很多文学杂志常常不翼而飞。有时候只能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去补读漏看的一些小说。
1987年初,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顶着寒风,满北京的报刊亭寻找1月号的《人民文学》,因为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期杂志被查封。后来才知道,刊发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就是朱伟。
有同学找到了这期《人民文学》,我赶紧把那篇惹祸的小说看了一遍,禁果总是很甜。同学们坐在宿舍里讨论这篇小说,大家都觉得禁得莫名其妙。
现在谁还讨论文学啊。
80年代那批作家的作品,我是挑着看的,实际上看得不多,我偏爱王朔和贾平凹,喜欢王朔,是因为他的匪气,且有情怀,这也是我后来不喜欢冯小刚流里流气的原因。大学时我们就把王朔的《顽主》改编成广播剧,在校园里播放。喜欢贾平凹,是因为喜欢他笔下描述的商洛的风土人情,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
2007年,《三联生活周刊》做王朔的封面故事,朱伟说,你既然喜欢王朔,你去采访他得了,你们俩肯定能贫出点东西。我斟酌再三,觉得王朔对我影响太大,见了他我会尿裤子,采访会变成一顺边,这是采访大忌,于是放弃了见偶像的机会。
最后我采访的是马未都、魏人和叶京。也正是因为采访马未都,我对80年代的文学编辑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此之前,朱伟从未谈论过他当年做文学编辑的事。
8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可比作家牛多了,地位相当于现在的风险投资人,作家都要哈着编辑。如果一个文学编辑发了你一篇小说,你的命运可能从此改变。想想吧,如果不是编辑发了余华的处女作,他今天可能还是一个诊所的牙医,你也根本读不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张艺谋也不会因为拍摄《活着》而最后被逼成国师,去导演什么开幕式或《长城》。
以我对朱伟的了解,他一定很享受当年做文学编辑被众人环绕的感觉,同时他也知道,发现一篇优秀的小说是他的职责,书里他常常提到因为没有抢到某个作家的小说而感到懊恼。但朱伟很勤快,常常骑着破自行车满北京找那些作家,采用人盯人的战术,从作家开始有创作想法,到最后作品完成,期间一定要盯紧。比如朱伟盯着莫言,希望他下一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当时莫言正在创作《红高粱》,等朱伟觉得高粱熟了,该收割的时候,发现《红高粱》被《十月》的编辑张守仁拿走了。
换别人,这口气就忍了,朱伟气不过,打电话给张守仁,又把《红高粱》要回来了,最后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这也有了后来张艺谋盘腿坐在朱伟家的炕上兴奋地想把小说拍成电影的想法。很多人不知道,朱伟是《红高粱》的编剧之一。
这是文学编辑在当时的地位。现在的文学编辑,大都是高级文字校对。所以,那个八十年代,只能重读,无法重返。
六
有一次,朱伟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好像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不是让我滚蛋的谈话。那次他聊到了关于记者写作风格的话题。在他看来,一本杂志,每个记者都应该有鲜明的写作风格,读者看着才不累,而不能写到最后同质化。
我那段时间正在博客上撒欢儿,嬉笑怒骂,反讽调侃。但是给周刊写稿子,我总是很严肃。朱伟鼓励我,认为周刊也可以刊发像博客上那样的文字。而我一直心有顾虑,毕竟这是一本还算严肃的杂志,一度我是拒绝用博客文风给周刊写稿子。博客是免费看的,你怎么写别人管不着。杂志是读者花钱看的,你不严肃,他们会生气的。所以,过了好几年,我才慢慢接受朱伟的建议,不然《西游记是一部公路片》这样的文字不可能发在周刊上。
看《重读八十年代》,我才知道,这种文风多样性的办刊思路是王蒙做《人民文学》主编时定下的基调,这也被朱伟移植到《三联生活周刊》上。
在周刊做主编时,朱伟不止一次鼓励大家放开写,并说自己写文章不好看。他写古典音乐的专栏,读起来确实有些枯燥,像是教案。后来他开了《有关品质》的专栏,写得又过于端庄。
但这本《重读八十年》的文字,读起来倒是很鲜活。朱伟擅长写过去的人和事,也可能是没了杂志的篇幅限制,有些文字,夹叙夹议,可以沉着自如,娓娓道来,非常好看。比如他写去美国在李陀家里包饺子吃,写跟余华一起看世界杯……字里行间,也能看出朱伟还是有些许幽默感的。
通过这些文字,能看得出,朱伟对那个时代,和那批与他一同成长起来的作家的经历充满了眷恋之情。更重要的是,他把这几位作家重要的小说都捋了一遍。
期待他的《再读八十年代》。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