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回北京,岂航(幽默书店创办人)跟我说,他要去养老院看侯牧人,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也正想看看他老人家,于是约好一起去。那天同去的还有乐评人金兆钧老师和原喜洋洋唱片公司的代永强。
见到老侯后,金老师送给他一本《无谓光荣,但逐梦想》。侯老师说:“你这本书我都收到了三本了,不要再给我了。”有些作者出书后总喜欢送人,有时送到连自己记不清送过谁了。金老师说:“小峰,要不送给你吧。我不知道今天你来。”于是我有了这本签名送给侯牧人老师的书。

我跟金兆钧大约是在1993年认识的,怎么认识的我记不清了。但我知道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89年。那年3月,崔健在北展办了两场演唱会,我看完后特别激动,写了一篇文章,写完后不知道投到哪里,于是想到了《北京青年报》,我骑着破自行车从蓟门桥到天坛公园附近,把稿子交给了《北京青年报》一位姓蒋的编辑,然后每天都盼着自己的稿子发表出来。盼了几天,盼到了一位叫金兆钧的作者写的评论崔健北展演唱会的文章。于是我只好再次骑着破自行车到天坛,把稿子从编辑手里要回来(当时没有复写),然后把这篇稿子投给了上海的《音像世界》,几个月后稿子发表了。
这件事让我记住了“金兆钧”这个人,后来会留意他写的文章,我那时还不知道,编辑喜欢脸熟的作者,而我只是单纯地以为,编辑发表他的文章,那一定是他写的比我写得好——那篇文章也确实写得挺好。
后来金兆钧的文章看多了,我大概明白了一件事,好像只有他在媒体上写流行音乐,很少看到别人写,别人写基本都是批评否定流行音乐。
那时候我还在上学,但总想着有一天要会会这个叫“金兆钧”的人,直觉是他懂的真多。
话说到了1993年,广州中唱的陈小奇带着李春波、甘萍、陈明、张萌萌到北京做宣传,李广平(广州中唱企宣)叫我过去玩,活动结束后去他住的酒店聊天,屋子里除了我们俩,旁边还有陈小奇和金兆钧。
那时我跟金兆钧还不熟悉,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就听金兆钧跟陈小奇说:“好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观点,这不前些天有个叫‘洛克’的人写文章还跟我商榷……”
我小声跟李广平说:“他说的那个‘洛克’就是我。”
再后来,我跟金兆钧混熟了。我一直称呼他“金老师”,别人都喊他“金爷”。我一向对中国人这种泛血缘式称呼感到别扭。尊者为师、能者为师。金兆钧是老三届,社会经验丰富,跟他聊天总能学到不少东西。“金老师”叫了30年,从未改口。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骂黄燎原胡拼乱凑、错误百出的《世界摇滚乐大观》,金兆钧见到我就说:“有人做这件事总比没人做好,至少让大家能了解到摇滚乐。”我说:“全都是错,那不是以讹传讹吗。”他说:“有本事你出一本啊。”
几年后,我把136万字的《欧美流行音乐指南》放到了金兆钧眼前。当时心里的潜台词是:“不要跟我叫板。”
这就叫年轻气盛。搁现在,爱谁谁,跟我有啥关系。
有一年去深圳参加一个流行音乐活动,活动结束后,我约金兆钧去吃宵夜。我喜欢听他胡扯一些音乐圈里的轶闻八卦,因为这些拿不到台面上的事,只有私下里聊天才能听到。我印象中凌晨四点钟回酒店时,金兆钧身后有二十来个啤酒瓶子。我那时不喝酒,因为听得太过瘾,我竟也喝了两瓶啤酒。
我跟金兆钧在音乐圈里的交集时间算下来并不长,从1993年到1998年,之后我对中国音乐没啥兴趣了,后来我去《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本以为可以告别音乐这个领域,哪怕让我去采访戏曲、扶贫、奇技淫巧呢,但还是被安排去采访报道音乐行业里的事,所以有一搭无一搭跟这个行业又打了几年交道。而金兆钧一直在这个行业里,用“浸淫”一词来形容不为过。所以他是一本冒着啤酒沫的中国流行音乐百科全书、十万个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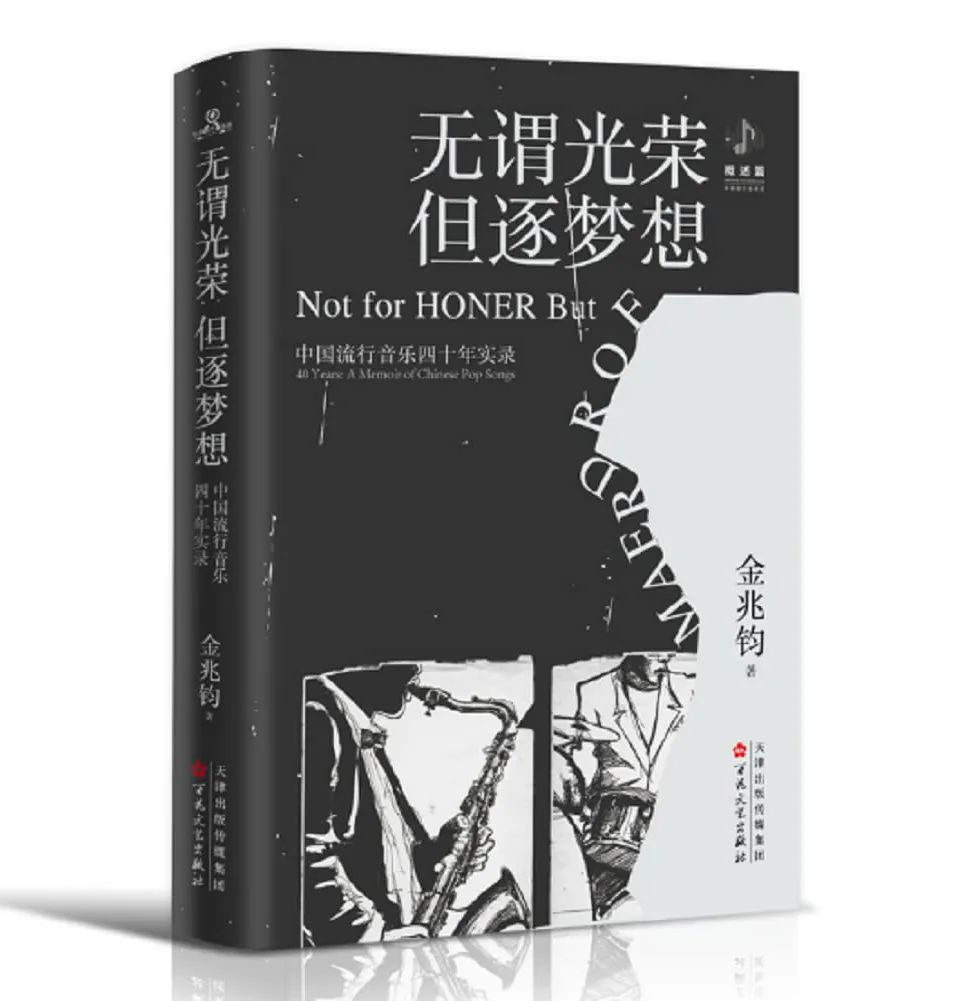
说说他这本《无谓光荣,但逐梦想》吧,既然无意中获得这本书,就更该珍惜,因为我跟金兆钧都遭遇过出了书送给朋友,朋友转手就卖给二手书店的经历——而且还都被作者及时发现了。
这本书基本上记录了过去40年中国流行音乐发生的事,如果你对这段时间流行音乐发生了什么事感兴趣,看看这本书,至少能掌握一个全貌,大事小情都没落下。或者你想了解过去流行过的歌曲,一种方式是你请金兆钧喝酒,他全都能给你唱出来;另一种方式就是按图索骥,把书里提到的歌曲听一遍,你就了解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历史了。
金兆钧送我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这是个阉割版。”我读的时候也能看出来,有些地方不连贯、转折生硬,尤其是写崔健那部分。但是在我看来,金兆钧写音乐最大问题倒不是是否被阉割,而是他的顾虑,他写的那些人都是他经常要打交道的,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他过去写文章从来都用“看破不说破”的笔法,我也养成了看他的文字用即兴脑补的方式来把缺失的部分找补出来。有时候看他的文章觉得特别累,消耗脑细胞。这也是我为啥喜欢跟他聊天,听他胡扯,因为酒桌上没有顾忌,讲出来的是有血有肉有起承转合的故事。我对中国流行音乐的了解,多来自他的口传心授。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本书像这本书一样把过去40年流行音乐写的如此详细。我读的时候意识到,这本书是在金兆钧过去的那本《光天化日下的流行》和日常在媒体发表的音乐随笔基础上糅合而成,或者说是《光天化日下的流行》的扩充版。
所以,这本书天生有一个硬伤,信息足够丰富,但显得形神具散。书的副标题是“中国流行音乐40年实录”,实录确实做到了,但总感觉缺了魂。威廉·曼彻斯特写《光荣与梦想》也是实录,但从头到尾他都凝聚着一个魂——“新”和“变”——战后美国的变化。《无谓光荣,但逐梦想》缺的就是这个魂——你写这么多到底想告诉读者或那些不了解中国流行音乐历史的人什么呢?
如果我是编辑,看完这本书的书稿,第一件事就是给金老师打个电话:重写一遍!我在阅读过程中都感觉不到作者的性格。
以前,我写中国流行音乐,多以批评为主,为此得罪了好多人。但就事论事是一回事,写历史是另一回事。历史除了让后人知道的更多以前发生的事,还要让人在阅读时感受到快感。中国流行音乐这几十年间发生的事,其实是很好玩的,一点不夸张,这几十年掺杂了嬉皮士、波西米亚、朋克、后现代以及最原始最土的东西,五光十色的,看上去不伦不类,乱七八糟,互不搭噶,像一锅乱炖,好不好吃你得拿筷子仔细扒拉,但背后都有应有的逻辑。
看完这本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故事:陈小奇创作《涛声依旧》,因为他上学时总是拿旧船票蹭船坐,蹭了好多年。多年后暗恋他的女同学告诉他,是因为那个艄公是她爷爷,给他网开一面。于是陈小奇来了灵感,写出了《涛声依旧》。你看,中国流行音乐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这也说明,有头有尾的故事让人印象最深。
真正的历史写作不是《左氏春秋》那种,你想象一下,研究这本书的历史学家最后都是死于脑细胞枯竭。
以我对中国流行音乐的粗浅了解,它既不可歌也不可泣,它一直以来属于可割可弃那种角色,想到你了,用你一下。想不到你就扔一边。它一直靠自己努力才把自己给活没了。
在90年代,我一直有个期待,那就是法治完善,能把音乐版权保护好,这样能在一个真正市场化的情况下繁荣。但谁都没想到数字化时代来得这么快,中国流行音乐是全球流行音乐同归于尽的祭品中年纪最小的那一个。
2009年,我听说王昆身体不太好,当时我有个冲动,趁着她还在,想从她开始挨个采访一些80年代就开始从事流行音乐工作的人,试图写一本当代中国流行音乐历史。但我这个人特别懒,列了一堆采访计划,却没有执行。直到有一天我听说王昆老师去世了,也彻底断了这个念头。
我掰着手指头数了数,目前对中国流行音乐最了解的人只有金兆钧,再找不出第二个,绝对是个孤品。他完整目睹了当代中国流行音乐从出现到衰落的过程,关键是他跟相关从业者非常熟悉,已经不是近水楼台了,他直接在月亮上,写点什么都是信手拈来,而且也只有他能把这段短暂的断代史写出来。
所以,我期待金兆钧老师能写一本中国流行音乐故事的书,哪怕像郑逸梅那种写法就已经很精彩了。
多年后,当金兆钧面对中国流行音乐考古挖掘工地,是否会想起多年前洛克跟他商榷的那个下午?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